牛军、王栋: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16日举行的东方历史沙龙(第125期):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嘉宾为bat365的牛军教授与王栋副教授。

主持人: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bat365教授、法学博士牛军老师,牛老师在冷战史、党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都有许多非常棒的文章。另一位年轻的学者,是bat365副教授王栋老师。今天的沙龙主题与王栋老师的文章有很大关系,他去年10月在外交史研究顶级期刊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上发表了题为“Grand Strategy, Power Politics,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大战略、权力政治与六十年代中国对美政策》)的论文。该刊物作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SHAFR)会刊,是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世界最顶尖学术期刊。这是中国国内学者首次作为唯一作者单独在上面发表文章。该文运用大量中美第一手的最新解密档案资料,挑战了国际学界现有的势力均衡、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等有关解释中美关系的观点,强调了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变量在解释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中的关键作用。所以这篇文章是我们今天沙龙聊的一个重要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两位嘉宾。
王栋:非常感谢老师的邀请,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和大家做交流。去年十月我在《外交史》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对美政策的文章,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引起了很多关注。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从我的博士论文中提炼出来的,后来应《外交史》主编的要求,对文章视角做了一点微调。因为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围绕的是中美之间的互动,就是整个60-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这篇文章则着眼于中国对美的政策和态度。事实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更感兴趣的话题。因为美国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美国档案已经解密很多年了,学者们做了很多研究,相对来说我们比较清楚。相反中国的外交决策,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对美外交决策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系统利用新解密的一手外交档案所做的研究还是非常的少。在匿名评审时,几个评审专家对这篇文章的评价都比较高,认为它代表了冷战史研究最前沿的学术水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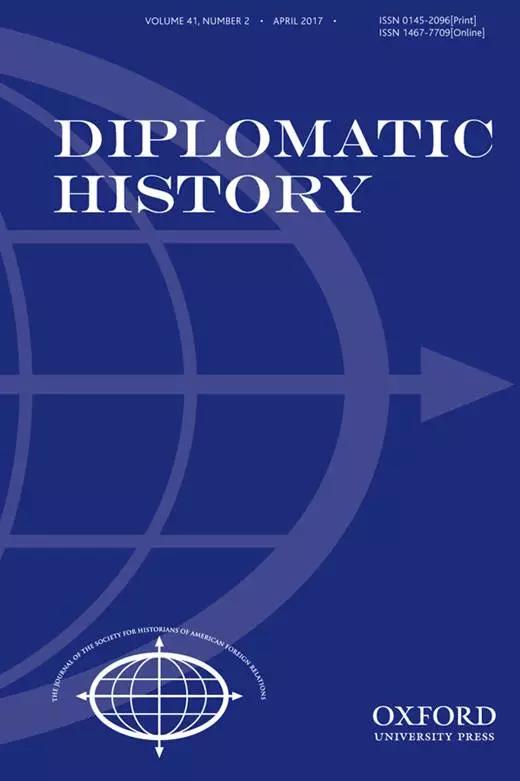
《外交史》期刊
提起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大家能想到最多的是尼克松访华和1972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段时间当然非常重要,例如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共识,都可以追溯到尼克松访华时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在建交上达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基石。从学术界的研究来讲。大量研究文献都集中在1969年后,特别是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这个阶段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我当年在写博士论文时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60年代的时候中美关系没有办法形成缓和,而是直到69年后,尤其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才逐步走上正常化道路?整个60年代中美之间延长性的、长期的对抗是怎么形成的?
回顾冷战研究的学术史,对于为什么会爆发冷战的解释,大概有三种说法:最早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认为是苏联的扩张引起了美国的警觉,美国要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威胁做出反应,因此爆发了冷战;再往后,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现实的国家利益,认为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了美苏的对抗;到了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由于一大批美国和苏东地区新解密档案的出现,开始形成了一个叫“新冷战”的研究领域。这时也出现了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和观念的重要性,这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建构主义、观念史兴起的大背景有关。
现有研究中,对于为什么中美在60年代无法实现缓和的解释,同样分三种观点:第一种叫势力均衡说,认为只有当面临苏联的共同威胁时,中美才会走到一块,后来尼克松来中国就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纵观冷战对峙的结构,1972年以前和1972年以后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苏联的威胁早在60年代就已经存在,如果是因为势力均衡,为什么直到1972年以前中美都无法走到一起?所以这种解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的。
第二种观点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了中美在60年代没法形成缓和,事实上1971年基辛格来华,此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中国依然是从世界革命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世界,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第三种常见解释是60年代的国内政治环境导致中美无法走上正轨。从美国方面来讲,实际上从60年代初的肯尼迪时代开始,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僵硬就有很多批评,支持调整对华政策的美国民意一直在不断的上升。肯尼迪很清楚这些民意的变化,他让自己的下属去收集了很多具体的数据,作为自己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因此关键不在于美国国内的反对,而在于美国领导人在总体战略上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的影响的。
我的这篇文章,核心观点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主流取向是恰好相反的。当大家都在讲观念的重要性,讲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时,我却回过头来讲权力政治的重要性。我的核心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在60年代采取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反美政策?这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它是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因此是一个非理性的政策?我通过大量的历史档案考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权力政治的考虑恰恰是反过来的,中国在60年代采取的强硬反美政策实际上是出于非常理性的战略考虑。所以我这篇论文的总标题是《大战略、权力政治与196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如果我们重新回过头看当时中国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定位会发现,中国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当我们仔细去考虑中国的很多对外战略上的考虑,完全不是像印象中那样,认为冷战时期,尤其是60年代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处于一种很激进的外交状态。这种激进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恰恰是基于一个很理性的判断。
简单的举几个例子。60年代初老挝爆发内战。老挝内战大体有三方,一方为西方阵营所支持,一方为苏联和中国所支持,另一方是中立派,战争的不断蔓延使得当时世界上的几个大国,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卷入到战争中。后来几个大国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对于老挝内战的态度。这个时候还是1961年,美国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次的反应很有意思,陈毅在讲话中说: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小小的国家,把几个大国都卷入进去。他强调我们一定要适可而止,如果不断的输出革命、支持老挝的游击队夺权全国政权的话,最后一定会引发美帝国主义的激烈反应,甚至加速世界性大战的到来,这对我们的建设是十分不利的。所以要打也是老挝内部打,我们几个大国不要卷入进去。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考虑。它说明我们的领导人当时在考虑对外战略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清晰地、现实主义地对中国所处战略位置、战略目标进行了审慎判断后才做出决策。
我这篇文章中还讨论的其他几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外交的激进化过程,这里面是否有失去的机遇?正如刚才讲到的1961年日内瓦会议,那时候陈毅等中国领导人说的很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和美国缓和关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但这不代表我们绝对不愿意和美国缓和关系,条件在于美国必须在涉及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陈毅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始终不愿做出让步,所以我们也不让。陈毅当时有个提法,说我们最多采用所谓的“日内瓦方式”,可以握手、可以碰杯,但是不做进一步的外交上的交流。
说到“日内瓦方式”,这要提到另一个有意思的外交细节。一直以来在中美关系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就是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总理握手,这成了冷战时期美国采取对中国敌视态度的一个象征。直到基辛格、尼克松来中国,跨过大洋的握手才象征着中美冷战的最终融化。但实际上有个细节是不对的。早在1961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陈毅作为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已经和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握过手了。对于此事我还找到了相关的档案记载,是陈毅在自己的讲话,里面详细回顾了相关细节。他说当时很多中间国家都对双方进行撮合,让中美之间拉拉手、说说话,因为中美对抗其实对很多国家都不利。在一个招待会上,陈毅突然发现哈里曼走过来站到了他边上,陈毅注意到了他并且转过身来,这时候哈里曼要主动和他握手,陈毅稍微想了一会儿也就握了。后来陈毅在讲话中还特意对握手一事进行了点评,他说握手是没有关系的,大大方方应战即可,至于中美关系如何缓和,那一定要看美国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上持什么态度,尤其是台湾问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二个部分讨论了中苏关系的变化和中国核武器试验的成功,在政治上象征着中国获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对于越南战争的升级,中国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包括整体的国防政策上面,当时毛泽东做了调整,把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战略修改为”诱敌深入“。还有个背景是中苏的分裂,在我的研究中提到了一个细节:1965年2月,当时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路过北京和毛泽东会见,这个会见很有名,在很多回忆录里都会提到。当时毛泽东说双方打笔墨仗没关系,可一旦帝国主义对我们动刀动枪,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团结起来了。可见当时虽然中苏双方有分歧,但在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上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威胁,那就是美国。

大家普遍认为在中苏大论战之后,两国关系就已经彻底分裂了,但我在外交部的档案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柯西金来的时候,中方对他的接待规格很高,基本上党政军各个方面的领导人都要出来宴请。柯西金在会谈中说其实苏联很想恢复中苏关系,双方还讨论了如何重新开始合作,例如经贸往来、互派职工等等。柯西金说苏联愿意再卖一些坦克和运输机给中国,但是周恩来是这么讲的:谢谢,坦克我们现在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可以从捷克斯洛伐克买来同样的苏制坦克。我们需要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这些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很重要,希望你们能够提供。可见中苏关系的变化是相当复杂的,包括中苏究竟是什么时候分裂的、为什么分裂?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考量。我看的这个档案至少可以说明,在1965年柯西金访华的时候,中苏双方是一度想把关系重新挽回来的。直到珍宝岛冲突,中国方面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苏联对中国安全上的威胁,才导致中美苏战略三角的逐步形成。这是对我文章的一个简要介绍,接下来请牛军老师发言。
牛军:王栋老师在我们bat365研究中美关系的新生代学者里是非常优秀的。他的这篇论文有很多新意,特别是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解读6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我对这篇论文感兴趣,是因为最近我恰好在写一个冷战时期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文章。60年代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这篇论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解读,用王栋的话说就是引进了一个新的变量,这是社会科学的常用术语。这也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社会科学发展提供的各种方法、视角,让我们能够用更丰富的视角层次、更犀利的工具来解读我们面对的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与今天有剪不断的联系,就是到底今天应该怎么认识中美关系?我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会受到王栋这篇论文中研究的时代的中美关系和我们对这个时代中美关系的各种解读结论的影响。
对于权力政治的问题,我想起来过去看过李泽厚先生一本书,叫做《实用的理性》,讲中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我现在结合对印度支那这场战争的政策研究60年代的中美关系,感觉王栋提的问题可以往更深层次上推进,推到中国外交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本质。我觉得这种实用主义传统在60年代的中国外交中依然起着作用。60年代的毛泽东在外交中充满了激情和革命浪漫主义,他追求世界革命、支援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援越南北方的统一战争、还有第二次亚非会议等等,这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将他个人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对世界革命的虚幻想象表现的非常充分,我们去接触档案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他个人那种强大的个性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如果不去深入阅读档案,去了解它的整个思维过程,我们会认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行为有很多潜在的负面后果,是毛泽东为了追求自己的革命理想,把中国的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这是一个常见的评价。
但我们深入阅读档案可以看到,在处理整个越南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在坚守着一条基本的底线,就是不直接卷入同美军的冲突,绝不同美国再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这条底线的存在,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1964年1月,黎笋访问莫斯科。前一年9月,越共中央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作出了大力向南方游击队提供援助的决议,包括派遣军队进入南方发动武装斗争等等。因为在8月的时候,美国刚刚支持了一场政变,把南方领导人吴庭艳给刺杀了,之后的南越政局一片混乱。但是越南劳动党中央总结之所以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是因为他们在战略上的判断有问题,太保守了。所以在九中全会越共就做出决议,要积极开展南方斗争、实现国家统一,包括把北方的建设问题也转向为南方的武装斗争服务。所以黎笋去莫斯科开会,路过北京就和毛泽东谈起了这个问题,最后提出了请中国派兵去老挝、越南。毛泽东告诉黎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是有争论的,尤其是老挝同中国接壤,如果出兵的话美国就会干预。果然,五个月以后美国就开始轰炸老挝,甚至把中国代表团给炸死了。毛泽东后来说他是不同意出兵的,认为老挝不要紧,同时告诉越南你们派兵去也要谨慎一点,因为老挝的那个军队战斗力不行,几次大战役都是越南人派兵过去的。可见毛泽东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有谨慎的一面,是非常复杂的。
很多年轻读者可能没有读过当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那个引子,叫《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里面讲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世界革命的形势、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所应该奉行的对外政策等等。这一时期是中共的激进外交理论形成最高潮的时候,但到了具体对外政策上,它绝不迈出引发同美国的战争那一步。可见当时的总体外交尽管是非理性的,但如果对一个盟友的支持要到把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的程度,这种情况只要能避免还是会尽量避免的。这个例子教训深刻,我们今天都应该继续,不要为了一个盟友把国家置于危险之中。
深入到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内部有争论的情况下,毛泽东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的口号一直非常响亮,那就是“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但仔细阅读这些都是有条件的,句式通常是“只要美帝国主义如何如何,我们就…”,其实美国它并没有想要进攻北越,只是轰炸而已。有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越南方面承诺,只要美国进攻你们,我们就怎样怎样。刘少奇在旁边提醒他说,美国可能不会进攻,只是轰炸,毛泽东就没有接这个话题。总之现实情况是美国从来没有进入北越,至于轰炸该怎么解决,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个人认为,王栋选择六十年代作为他的研究还是很有眼光的。六十年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在我的研究视野里,中国的外交史写作更多集中在七十年代,因为这是随着政治发展需求来进行宣传介绍的。七十年代虽然是文革,但是打开中美关系是文革毛泽东外交的一个重大的亮点,也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共继承的毛泽东各种政治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可能受个人兴趣的影响,我觉得六十年代是最值得研究的年代,因为这个年代是中国外交空前活跃、中国领导人空前的激动、毛泽东等人空前地热衷于外交事务的年代。大概五十年代有过一段,但是从没有像六十年代那样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把中国的外交看作是实现自己理想极端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那个时期的外交活动非常多,也可能和档案开放有关系,可能后来的领导人其实更关注外交。
但以邓小平为例。他在1979年访美后对身边人说,我的外交任务完成了,以后哪也不去了。之后18年他再也没踏出过国门,把全部兴趣的绝大部分放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上,也就是改革开放。他见外宾的经历都被搜集出来了,加一块也没说过多少话。他后来回忆说,1985年他托人给戈尔巴乔夫带信,说如果你能接受中国的三个条件——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我们就实现正常化。他的口气就是你到北京来也行,我也可以破例去莫斯科。那时候邓小平已经多大年龄了?他所说的破例,我看写中苏关系的人都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所谓破例就是79年访美结束后,他在飞机上对身边人说的那句话:“我以后再也不出国了”。但为了使中苏关系能够实现正常化,推动苏联新领导人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他说我破例了,哪怕你年轻不愿意来,我八十岁了也可以过去,可见他对国家所获战略利益的看重,用这种承诺的方式来推动。举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虽然档案没有公布,大概也能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事务的兴趣从来没有像六十年代那么浓厚,所以六十年代很值得专门的研究。此外六十年代的开放档案也非常丰富、数量巨大,这些是最基础的研究条件。也欢迎有感兴趣的听众加入到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
今年初,人民出版社和博源基金会共同出版了一本中美关系两百年的图册,这本图册收集了中美关系各个年代的照片,非常好看。前言中,王缉思先生提出了一个我们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学者叙述的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实是将中国作为中心的,按照这样的逻辑,至少我们中国人应该关注自己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例如根据这本画册的断代,中国人是以自己的历史来划分中美关系史的。我们讲近代中美关系史是以作为中国近代开端的鸦片战争来划界的,而非以美国的历史来划。之后的三个不同阶段——辛亥革命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都是按中国人的历史来给中美关系划分阶段的。可见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叙述这段历史。但事实上,我们过去对中美关系史书写中,并没有把中国自己放在这段历史的中心,对中国对美政策的书写、研究远远不够。。
例如,我们中国人之前写的最优秀、质量最好的中美关系史著作是陶文钊先生的《中美关系史》,从民国时期写到2010年。但里面大量书写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史,或许书名应该改为叫《美国对华关系史》。它的主体都是美国,视角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影响、调整过程,虽然时间上按中国历史断代,内容上却都是美国视角。
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的学术发展比较晚,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八十年代积累,九十年代出成果;第二是在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各个领域中,中美学术交流开始的最早,促成了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影响;第三就是美国档案的开放,数量大、内容丰富、透明度高,我们做历史研究就是这样,没有档案就不敢说话。我说做当代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场冒险,跟赌局一样,很多情况下你没有档案,单靠判断就有风险——有时候你做了半天研究,最后档案出来的时候就被推翻了。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海量的档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允许学者根据自己的规范去自由检索,我们的判断错误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判断上的失误进入到教科书就会影响接触这些知识的员工的思考质量。这个问题非常大。我们会重视食品质量问题、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但我们不重视知识的污染、精神生活的质量问题,但这方面同样会像不合格食品、说客空气一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精神生活的质量是我们生活质量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像王栋这样的年青一代,将来在这个领域是能有很大发展的。我是77届的员工,当我在反省我们这一代上学做研究的时候,我们看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书中影响最深的有三本:一个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个是丁名楠等人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还有刘大年先生的《美国侵华史》。在学习阶段,我们所理解的中美关系的核心部分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包括那个时代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等,基本视角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新民主主义也罢旧民主主义也罢、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这个主题是不变的。
9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研究成果已经大大的拓展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如何回过头来看并调整我们过去积累的这些知识,对于今天认识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对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什么样的主观知识结构驱使我们在每个问题上选择性地做出判断、形成情绪变成行为?先不说形成政策,我们这些不参与政策的人是怎么形成自己的情绪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现在的各类文献都像我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很多我们过去认为是定论的事情,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证明其实是双方可能都有问题。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不是学术结论,而是一个经验性的判断。中美关系的内容极为丰富,给历史人物提供了巨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你想选择对抗,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想选择合作,也同样可以找出足够的理由,最后那个站在舞台中间的历史人物可能是决定性的。我想我们每个人没有能力影响政策,但是我们能决定自己的判断。
王栋:刚刚牛老师也提了很多问题,我看看能不能尝试去做一些回答。首先是我这篇研究在整个冷战学术史脉络中的地位的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他重新回到了一种传统主义的解释范畴,也就是强调权力政治的重要性,是一种重视利益、战略、权力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在现代的历史研究中,不仅是冷战史研究,我觉得整个全球史研究中最时髦的就是讲文化、讲观念,这是整个学术界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件回归传统的事情,当然重点不在于时不时髦,而在于对历史的解释力。
另一个很有感触的地方,就是对历史的丰富性的精确理解和把握。自己前些年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外交史研究传统的文章,里面提到,我们对于中国外交史的理解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官方的框架里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一定要有一个官方的历史叙事,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讲,如果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理解都停留在教科书层次的话,理论上的研究就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因为官方的叙事毕竟是有一个特定的框架在描述历史的。不仅仅是员工,我们的决策者也会受到经验性的历史认知的影响,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和再认识确实很重要。
还有个问题也很重要。中美关系两百年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中国自己的变化决定的。但是看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却是反过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陈述自己的故事,没办法讲清楚中国自己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叙事和脉络。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材料。档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话语权。以陶文钊老师为例,陶老师的《中美关系史》当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著作,但从学术批判的角度来讲,确实是存在材料缺乏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档案解密制度并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是在不断进步的,随着国内档案的不断开放,也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好的基础。
我自己常对员工说,历史研究很有意思,写起来有点像写小说一样,里面有情景、有人物、有个性,还有各种戏剧冲突。但和小说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档案来写的。再举个例子,比如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美苏的战略三角就逐步形成了。这里面有很多互动的细节。当时苏联也很着急,因为它也搞不懂中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担心中国那个时候会不会和美国走到一起,那样战略上就会给它造成压力。所以苏联就派出很多代表团到各国去游说,要论证一点什么呢?就是中国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很危险的民族,我们要共同对中国进行遏制。当时苏联领导人提出要构建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采取了一些报复性的动作,如在新疆中苏边境对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伏击等等。
但苏联却失算了,这件事反过来促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三角里,我们应该选择站到中国这一边。当时苏联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一些总参的高级官员去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会谈,关于这个会谈我看的是美国方面的档案。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反复强调,与中国的珍宝岛冲突这件事无足轻重,没有什么大不了。苏联为什么要这么讲?如果它承认了这件事对苏联构成了极大的影响,使其在战略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那么在这个战略三角里、尤其是美苏关系上就要处于一个劣势,所以它一定要强调珍宝岛冲突这件事无足轻重。苏联代表团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珍宝岛本身是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岛,冬天那里是结冰的,可以通行,所以才爆发了这样一个摩擦,等到春天来得时候河水上涨,这个问题就没有了。美国人也不傻,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逊听到这个解释都快笑出来了,他很有自我调侃精神,说我也希望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也能像你说的一样,春天来了河水上涨后,这个问题就没了,比如我们在越南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历史学者可能还需要一些判断和直觉、想象力和灵感,这样才能做出一些很扎实又有创新的研究。



